|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社会史
地方上的社会组织
从各种观点研究汉代社会的学者们觉察到了村社组织中的重大变化。在帝国以前时期,相对封闭的、往往以大姓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相似的、其成员协力从事农业和其他基本生计的村社被认为是地方组织的普遍形式。从董仲舒到崔寔和仲长统的汉代文人都具有这种意见。在前汉以前开始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被认为把这种村社破坏了。某些现代学者认为货币经济造成了使原始的、以大姓为基础的地方村社瓦解的阶级差异。另一些学者认为村社的封闭领域是被沟通各个村社界限的集团强行打开的;这些集团包括商人、难民、漂泊的劳动者以及同上层社会有联系的豪门。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完全消极的过程,是农村的休戚相关与平等被经济与社会剥削代替的过程。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由于经济进步力量和帝国的政治一体化造成的一种即使不是积极的、也是不明显的发展过程。[1]
鉴于汉代中国在地理上的巨大差异,旧方式变化速度的不同是不足奇怪的。在商业和政治发展最巨大的地区,在人烟稠密的大平原和主要交通干线附近,似乎存在着高度的迁移率,劳动者到处流动以寻找工作,商人和官员带来了最新的想法、技术和产品。因为农民能够依赖政府来保持良好的道路、稳定的货币、法律和秩序,甚至救济计划,故他们能够种植商品作物,挤进商界,和成为工匠或工资劳动者。
尽管有这些社会变化,但以血缘为基础的地方集团(豪门大族)在整个汉代似乎仍然是普遍的和有势力的。当这些血缘集团制造麻烦时,史书上常常提到它们。一个例子是北海国的公孙大姓。后汉王朝的奠基者光武帝在位时期(25—57年),公孙丹被任命为北海国相。不久,他指使他的儿子杀死一名过路人,把尸体作为他新住宅奠基的祭品。当太守处决他们父子二人时,公孙丹的三十几位亲属和追随者武力闯进相府,寻求报复。[2]
大多数豪门大族在地方上不如公孙大姓那样有势力,因此,给政府制造的麻烦要少一些。在公元160年的一件石刻上发现了关于这类地方血缘集团的罕见的材料,段光在该石刻中叙述道,当他到公元前6世纪楚国大官孙叔敖故乡去任职时,他梦见孙叔敖。段光极为惶恐不安,于是立庙祭祀孙叔敖,并寻找孙叔的后嗣来主持祭祀事宜。他发现该地有三个孙叔血缘集团(宗),每个集团都以其聚居地来称呼。每个集团都无人受过教育。他们的传说是,孙叔敖有一个后人在前汉任太守。他的儿孙都在地方上担任下级官吏。后来,在前汉最后10年间,这个家族遭到土匪杀戮,只留下三个不满10岁的男性同辈人,他们都无力受教育。现在的几个血缘集团是这三个男孩的后裔,从那时以来,他们的成员务农为业,无人读书了。[3]
但是,有效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在汉代早期就破坏了地方上的和血缘的团结关系,到公元2世纪,政府不再决定地方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公元140年以后,政府逐渐丧失了提供救济的能力;随后丧失了维持特定地区秩序的能力;最后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旧的大姓组织中相对地说未受秦、汉国家实行的社会变革影响的那些村庄和村社往往能照旧延续下来,除非它们位于被严重战乱破坏的地区,除非当地人民因而被迫加强了自卫的能力。农村社会比较发达的部分受到更为严重的危害。因为不能把在以前诸世纪中已被破坏的旧的血缘纽带和地方村社重新建立起来,故必须找到共同保护的新形式。
在公元184年爆发的内战以后,[4] 地方宗教团体的势力已十分明显了。大概在公元1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人烟稠密和有相当数量离乡者的华北地区出现了若干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强调诚信和忏悔。它们提出以诚意治病和不久将天下“太平”的希望,人人像一家人一样。在东部平原,太平道的信徒在宗教统治集团领导下掀起一场组织得很好的叛乱,杀死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地方官员。正规军很快打败了他们。[5]
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西部,另外一些宗教团体进行自卫,以防发生当时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它们甚至为难民提供避难所。五斗米道的领袖张鲁成为2世纪80年代至公元215年巴郡和汉中郡(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的实际统治者。他通过起义队伍统治集团中的宗教官员治理这片地区。他按照政府驿站的模式设立义舍,但义舍对所有的人开放,并供给谷物和肉食。希望过路人得到他们所必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拿多了,鬼道会使他们生病。曹操得知张鲁的势力以后,于公元215年打败了他,曹操称他是善良人,并授予他和他的五个儿子以封地。[6]
在不大发达的华南地区,农民们没有如此频繁地加入宗教团体,也许是因为村社组织仍然强有力和构成了自卫的适宜基础。[7] 同时,到后汉末年,一位到豫章(在江西)任职的官吏报告,政府官吏在那里遇到了棘手工作:⑤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华子鱼所遣长吏,言‘我已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
平定这帮大姓(史称“大姓匪帮”)是汉末10年间孙氏家族力图巩固南部控制的重大任务。
这个时期出现的地方组织的另一种普通形式不是由农民及其宗教或血缘关系的领袖所组成的集团,而是由地方豪强及其党羽所组成的集团;这些人常常包括亲属,但是这些集团似乎不是像大姓一样组织起来的。当184年以后爆发全面内战时,人人在全国各地开始招募党羽,组织联盟和建立私人军队。另一些人则率领人民进山寻找避难所。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一开始未必招募军队,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客兵”、“部队”、“家兵”或亲属。
在某些场合,这些党羽是某人的佃户和劳动者;在另一些场合,他们似乎是自愿参加自卫团体的人,这些自卫团体是前一代建立起来的,用以对付法律和秩序横遭破坏和时不时的农民暴动。[8] 在四川,当声称与黄巾有联系的当地造反者打败官府时,一个下级官吏调动数百名家兵,然后又招募千余名其他人员,终于赶走造反者。一个参加孙策(175—200年)部队的人,在起义以后不久带去100名“私客”。另一位加入刘表(死于208年)部队的人,带去了他长兄早先从农村招募来的几百名“部曲”。[9]
正史反映了关于这些地方领袖和他们掌握的实力的两种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因集合忠实信徒,并用信徒公正、有效和宽厚地治理地方,而赢得同时代人的尊敬。[10] 如果这些人平定暴动,他们便被当成英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被认为是对于朝廷命官有效控制的威胁,因为可能妨碍命官行使正常职务:维护法律和秩序或征募应该服役的人。[11]
虽然这些豪强和扈从的社团与在王莽统治的衰微年代出现的社团之间有类似之处,但必须指出两点重要区别。首先是数量上的区别;在后汉末期,甚至在国内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也被描述成不只拥有几十名,而是拥有成百成千名经常依附的部曲。第二,在较早的时候,需要自卫的时间比较短,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不超过10年。相比之下,在公元2世纪40和50年代一旦开始经常发生叛乱,直到隋、唐才恢复标志汉代鼎盛时期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在缺乏有效的国家控制的情况下,建立在必须互相保卫和互相援助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形式成为这个时期比较持久的特征。
社会层次
有两种标准用来表示后汉“上层阶级”的特征,一种标准是以汉代社会荣誉的范畴为根据,特别是以有教养绅士(士)的身份为根据,另一种标准是以经济或政治力量为根据。在传统上,中国史学家采用“士”这个字眼表示社会中坚分子,但是,现代大多数社会和经济史学家回避这个字眼,其理由是,这个概念不大符合实际,它含有一种成问题的道德高尚的意思。他们不采用这一术语,而采用“豪族”这一术语来表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地方上的地主和其他有势力人物。[12] 每一种区分特权阶层或统治阶层的方法都有其优点,但是不要把不同的标准混淆起来,因为不是所有被公认为士的人都可被归入有势力地主这一类。在这里,“上层阶级”这个术语表示自认为“士”和被别人承认为“士”的那些人。
社会层次在后汉期间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的底层,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大庄园的发展方面和地方社会的重新改组方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变化。这就是说,许多以前独立的平民由于经济困难或必须寻求保护而被迫成为依附的佃户或部曲。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和在别人的头脑中,这样一个步骤招致社会地位的丧失。
社会的较高层次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社会上迅速向显赫和权力的最高地位升迁的机会似乎已经减少了。另一方面,地方上的社会名流不断加入全国性的上层阶级(即有教养的绅士或“士”),因此,实际上上层阶级显著壮大。这样,太学中有抱负的门生倒是可能正确地感觉到他们没有多少升迁的机会来成为一名大臣或高级从政者,这种在机遇上的减少只部分地归因于体制上更加僵化。这也归因于自认为是高级官职潜在候补者的人数增加了。
有教养绅士即“士”的概念是后汉关于身份的观念的基本概念。起码从孔子时代起,“士”这个字被用来表示在德行上和文化上证明有资格担任国家官吏的那些人。这些人包括教师、赋闲绅士和官吏。在广大的绅士集团里面存在着几个公认的等级,这些等级是以对于某些传统的精通程度、某些有价值的职业和领导权限来标志的。在后汉初年,桓谭(公元前43年—公元28年)对于上层阶级内的等级制度作了简明的描述,而区分出五个等级。
乡村的士以其关怀和忙于家族事务而著称;县治一级的士精通文学;郡一级的士忠于其上级,是正派的行政官;中央政府一级的士是心胸宽大和有才能的学者。在所有这些士之上是国士,这是一些其才能远远胜过平民的人物,他们思想丰富,具有远见卓识,他们能规划天下大事,并取得巨大成就。[13] 可见,按照桓谭的分析,士的地位取决于道德品质、文学专业才能、聪明和才智,而他似乎认为那些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将获得适当的官职。
桓谭认为“士”必须具备的所有这些特质实际上是主观的。因此,承认为“士”的条件取决于孝顺、忠诚、豁达和有才能这些术语所具有的意义。哲学著作在赋予这些术语的意义方面起了某种作用,但是,后汉期间“笃行传”的流行形成了塑造人们理解这些特性的另一种也许更为重要的方法。这些是个别人物的传记,他们之所以被人们铭刻在心,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或理性生活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是高尚品格的典范。把他们的经历和行为记录下来,便为当时绅士面临的挑战和互不相容的要求提供了戏剧创作的材料,从而创造出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社会与政治状况的形象和隐喻。应劭(约公元204年逝世)在其《风俗通义》中讨论了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流传的许多传记性的轶事,通常是为了批判他认为的关于他们正当行为的那些传闻。在若干情况下,他记录的轶事终于出现在《后汉书》的“笃行传”中。[14]
笃行的一个可信赖的例子是《后汉书》中的王丹传。王丹是一个典型“乡绅”。他处于向后汉的转变时期,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他住在老家,利用他的大部分财产救助穷苦人。每年在农忙季节,他带着酒肉到田间去奖励勤勉的农夫和责备懒汉。据报导,在他的影响下,全村富了起来。他也使一些家族重聚,并立下了丧葬的规矩。在内战期间(约公元24年),他带领男亲属给军队捐赠了两千蒲式耳(斛)粮食。[15]
王丹的“言行”有助于确立地方上家长式领导权的意义;另一种笃行表现了孝顺、忠心和诚实的有关美德。乐恢生活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当他的父亲——一名下级县吏——由于某种罪过听候处决时,当时年仅11岁的乐恢一直站在大门口等候着,他终于感动县令允许赦免。后来,当乐恢在一位老师那里求学而这位老师被拘捕时,他为老师辩护。当他为之效命的太守被处决后,他是敢于担负起殡葬的唯一的下级官吏。当他担任郡的书佐,为郡府主选人员时,他从不徇私,他甚至选诽谤他的某人之子为“孝廉”。乐恢最后任职中央政府,但他不眷恋权位,而回到他的本村。当窦宪的势力十分巨大时,他服毒自杀,数百名弟子为他送葬。[16]
对于社会结构的批判
当知识分子对于后汉的社会制度发出怨言时,他们并不反对桓谭规划的社会模式。他们反对的只是这种理想制度未能实现。具有伟大天才和伟大品格的人物不能侧身于高级政界;庸碌之辈反而有很大势力。另一种怨言是,在鉴定一些人——特别是出身名门或富有的人——时,要照顾到与德才无关的因素。王充(公元27—约100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年)两人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王充来自东南会稽,其曾祖是地主,祖父是商人。据王充记载,他们也是地方上一霸,这个传统被王充的父亲和叔伯继承下来了,结果是家里两次搬家,以逃避他家的仇人。王充6岁时他父亲开始教他念书,8岁时把他送入有100多名其他男学生的学校。王充在其随笔的一处振振有词地问道,是不是他的祖先没有得到学术或文学成就的名声使他不能获得这种成就。王充在回答中辩论道,真正的卓越人物是靠个人,而不是以出身名门的身份出现的。但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17] (他依靠在洛阳书肆上阅读书本的办法,解决了他家里没有书本的问题)。[18]
王充的《论衡》有三篇论述儒生和文吏的相对价值的问题。[19] 在桓谭的体系中,确定荣誉的是道德品质和知识才能;官阶只是相应的伴随物。可是根据王充的说法,大多数人只尊重官员的地位;他们称赞有能力、但读书不多的文吏,瞧不起没有做官的儒生,认为他们没有经验和不中用。王充关于典型官吏的描绘显然是讽刺性的:[20]
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
在王充看来,受过圣教薰陶的人应该比这样的官员受到更多的尊重。
四、五十年后,王符同样愤愤不平。虽然这些道德家经常称赞贫穷而正直的学者,但是王符认为缺乏钱财妨碍地位的提高。他指出了对于贫困的普遍偏见和人们把他们一切行为误解为损人利己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来访问,便认为他们傲慢;如果他们来了好几次,人们便以为他们是来讨一顿饭吃的。他也抨击了当时所有人渴望公职而需要与有钱有势的人物建立良好关系的现象;他抱怨说,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正直的学者过退隐生活,狡猾之徒则由于他们的关系网而赢得了对他们成就的巨大褒奖。[21] 王符在另一篇短论中写道:“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在他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22]
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人之善恶,不必世族。
表17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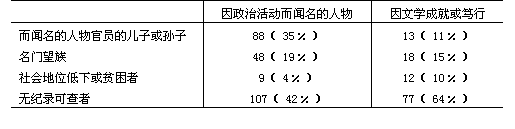
社会变动性
从《后汉书》中可以看出,王充和王符关于希望上升到取得全国权力与功名的人物面临种种困难的怨言有许多可信之处。正史使人感觉到大多数获得功名的人出身于在地方上已定居数代之久的名门望族,许多家庭已经有人为官。如表17所表明,在252位正式立传(或者因政治成就闻名而集体立传)的人物中,1/3以上是官员的儿子或孙子。除此以外,总人数中几乎有1/5出身于这样或那样地被描写为显赫的名门,通常所用的词汇如:“郡县大姓”,或“世代为官”的名门。
在大多数其他传记中,没有记载人物背景;只在少数场合,个别人物似乎出身于社会地位显然低下的家庭,或者出身于非常贫苦的家庭,以致必须干活才能求学。甚至在120篇因学识、品德、文学才华或独到的思想而被称赞的人物的简短笃行传中,只有5篇似乎是上升到社会上层的真实范例。[23] 在这批人中和在政治上活跃的集团中,其他一些人物被描写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孤儿,但这种贫穷常常只意味着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必须替别人干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证实了他的非凡的决心。
《后汉书》描写了异常长期地处于显赫地位或社会地位异常迅速上升的少数实例。吴汉(死于公元44年)出身于贫苦家庭,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开始其政治生涯,但是在王莽统治末期,他受到了重视,升任掌管军事的高级职务和享有显贵称号。第五伦(盛年期40—85年),后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富有资历的政治家,出身于前汉非常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在汉朝初年被迫迁往长安,作为削弱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最亲近的亲属似乎并不显眼,他因组织抵抗一次暴乱而开始受到官方重视,此后,他当了一名县吏。当他觉得一事无成时,他弃官经商。后来他在长安当官,从此发迹。[24]
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但是不能指望出身比较低微的人在其一生中能够爬上高级职位。公元1世纪末,虞经(他在故乡郡县任狱吏达60年)希望他的子孙升任重要高位,这被认为是离奇的奢望。据报导,虞经说于定国的父亲是县里一名书佐,他却擢升为丞相,因此虞经自己的子孙可以升任大臣高位。这个故事可能载入《后汉书》,因为虞经的孙子虞诩确实擢升到掌管尚书之职。[25]
长期显赫的实例在历史上多得很。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应劭(约死于公元204年)出生于已经有六代人为尊贵官员的名门。羊续(公元142—189年)的七代祖先中有太守、大臣或都尉。贡禹(盛年期165年)家族在七代人中产生了53位大臣和太守、7位侯爵。[26] 此外,在后汉时期,门第似乎被公认为担任某些职务的法律根据。从公元86至196年这110年中,在三公中起码有一位是羊家或袁家成员的时期有46年。在较低的水平上,在整个后汉期间,一个因有法律专家而闻名的家族(颍川郭家)产生了七名廷尉和其他许多法官。[27]
《后汉书》也揭示出,如王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想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崛起的强烈愿望是那些已经可能侧身于最高社会和政治集团的人们的共同现象。保存了关于一些人的轶话,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才获得了孝顺或谨守陈规的名声,为的是要取得“孝廉”的美名和侧身于正规的文职机关。那种熟谙大人物的生活,但对于功名仍然感到淡漠的罕见的人物,被人们敬畏地几乎视之为超人。
地方精英
后汉王朝的上层阶级被限定包括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绅士,他们至少受过起码的教育,他们熟悉行为规矩。在社会学上,这个上层阶级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他们活动的地域为根据。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郡县的下级官吏;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省级官吏;另外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活跃于京城和在中央政府任职。但是,这些活动等级之间的区分并不严格,那些有才华或有野心的人物很容易越过这些界限。
但是给地方精英——仅仅活跃于郡县等级的上层阶级中的那一部分人——作出适当的描述是困难的,因为使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地方权力结构与地方精英非常之少。所以,大量后汉史料对于这类人只提供了非常不完全的看法。地方实力派人物引起了那些面向中央的人们的注意,通常是因为他们滥用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干扰太守或县令收税或维护秩序的工作。尽管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地方精英是唯一重要的行使权力的人物,但是关于这些人物在他们村社中所起的作用则说得很少。
幸而保存下来的后汉数百件石刻铭文,提供了关于地方社会的比较详细的看法。这些铭文是为地方而书写的,为的是把对于特殊团体、村社或家族的有意义的事件或功绩记录下来。[28] 其中有许多是县绅为了纪念调任别处的卓越的县令或者是为了纪念寺庙或桥梁的建筑而书写的。这些县级碑铭中有11件刻着发起人名单。例如,为纪念酸枣县令刘熊(公元2世纪)而立的石碑刻有一长串捐献者名单,按照这个次序排列:4名退隐的正规官员,32名退隐的州郡级官员,25名县级官员(这位县令以前的下级官员),15名荣誉县级官员,55名赋闲绅士和43名门生。[29]
如同别的名单一样,这个名单上的县里工程的捐献者大多数是在职或退隐的下级职员和“赋闲绅士”。虽然几乎没有一人因身为地方绅士或下级官吏的功绩而有资格在《后汉书》立传,但是某些著名人物有喜欢这种生活的亲属。马援(后汉第一代著名将领)的从弟喜欢这种绅士的简朴生活;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公元2世纪后期,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和两位元老的侄儿宁愿超脱于京城政界之外,分别选择了隐居的乡绅、学者和郡治下级官员的生活。[30]
从铭文看出,许多人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地方绅士或下级官员而感到自豪,渴望关于他们成就和功绩的纪录能够保存下来。不过,他们也遵守内部等级制度。在大多数碑铭中,下级官员不仅使自己与他们上面的正式官员以及他们下面的赋闲绅士区别开来,而且把他们自己分成两个等级,在太守或刺吏下面供职的那些人为一级,在县令下面供职的那些人为一级。这种区别看来很重要。郡里的下级官员处于直通中央政府的阶梯的最低一级上;县里的下级官员没有这种地位。
在《后汉书》中立传的许多人以及其墓志铭保存下来的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郡里的下级官员开始发迹的。铭文往往列举了依次担任的所有职务。例如,武荣(约死于公元168年)在完成学业以后,在省里当书佐;然后他在郡里任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和担任功曹的守从事,最后在36岁时被举荐为“孝廉”。[31] 此外,在同一家族中,某些人可能顶多不过高升到郡里或州里的下级官员,而其他人则可能成为正式官员。
下级县吏常常从下层社会选拔。碑铭没有提供那些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任职(或公认任职)的人们然后擢升到较高职位的例子;也没有在郡里当下级官吏或正式官吏的人们承认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下级县吏的例子。《后汉书》在叙述这样一些实例时,通常也包括一些不常见的情况。下级县吏擢升的最平常的原因是在他管辖的地区遭到进攻时他显示出军事才能。大多数这样的例子发生在这个王朝的初年或末年,当时战事频繁,非常需要有能力的官员。
如果军事才能不是一种因素,个人的抱负则起显著的作用。一个适当的例子是著名学者郑玄(127—200年),他年轻时曾任下级县吏。在他父亲眼里,这个职务是非常合适的,而认为郑玄对于学业的爱好是不足取的。但是他父亲的反对未能阻止郑玄在学术上的抱负,他终于放弃这个职务,到京城继续求学。[32] 因此,如果从地方精英(而不是像王符和王充那样的文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地位的变动,决定性的步骤是到县外去发迹。对于想一生留在家乡的人来说,县里的职位是令人满意的;对于想侧身较高集团的人来说,最好是到郡里觅求一个下级职务,或者甚至到京城去完成学业和碰上重要人物。
我们的全部史料显示出亲属关系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后汉书》提到了郡县大姓或名门。以慷慨行为和受人尊敬而闻名的人物反复被描述为给他们本地亲属赠送财物。但是,通常从《后汉书》看不出是不是地方上的整个亲属集团都属于地方精英,或者他们只有少数人是精英,其他人则是普通平民。石刻显示出,在许多场合大批同姓或同宗人积极参加县里事务。在关于钟姓亲属修缮神话中的贤明尧帝及其母亲庙宇的工作的两份记录中发现了最明显的例证。[33]
城阳钟家无人在《后汉书》立传,但是在公元2世纪中叶,钟家有一位退隐大臣,他组织钟家的“贫富”亲属参加这些事业。进行捐献的有4名正规官员、6名州级和郡级下级官员、19名下级县吏和一名青年。因此,钟家可能有许多贫穷亲属,他们只能捐献劳动力,但是至少有29名成年男人拥有某种官员身份;不过其中2/3是县级官员,他们在县里可能是靠勤勉获得职位。
民用铭文很少详细说明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但是,往往有那么多同姓人,以致能够合理地推断出某种亲属关系。例如,在作为对一位被调职县令表示敬意于公元186年建立的碑刻发起人而列举的41人中,有26人姓韦,12人姓范。[34] 这样的县级工程发起人名单总共有11份,而且除了其中两份外,至少有一个家族的姓经常出现;在其中四份中,有一个家族的姓占这些名单中的姓的20%以上。在有100多个姓的三份名单中,每份名单都证明几家名门以及同一姓的官员、下级官员和非官员同住一地。例如,为对一位县令表示敬意而于公元185年建立的一块碑刻的157名发起人中,24人姓李,14人姓苏,13人姓尹。[35] 表18的数字表明四个地方亲属集团中存在着官员、下级官吏和没有官职的人。[36]
表18 县里发起人名单上推测为亲属的官员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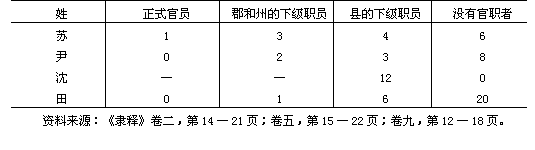
上层阶级中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
后汉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有许多染上了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的色彩,这种关系使人们从等级上发生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被保护人有两种主要类型。[37] “以前的部属”阶级总是产生由别人指定或推荐职务的人。中央政府的少数高级官员在其衙门拥有大量职位,他们可以自行挑选人员来担任这些职务。太守、刺吏和县令也可以委派数十名下级职员。特别是太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他举荐地方人士为“孝廉”,因而能够和日后在官僚机构中也许会高升的人们建立恩惠关系。第二类被保护人称为“门生”。在理论上,这些人蒙受庇护人的恩惠,因为他们接受了他的教诲。庇护人可能是真正的恩师,但是正式官员也收受门生——被保护人,门生投奔他们,不是为了获得教诲,而是寻求帮助和庇护。
公元2世纪期间,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日益巨大的政治意义。这种发展也许是私人关系和惯例获得巨大重要性,而官方的和公共的关系则被认为不大重要这样一种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同这种新情况有关系:孝顺和公共责任感的美德已被列为人的价值的尺度。正像指望一个人始终忠于他的亲属和他的邻人一样,他也应该铭记他以前的恩师和长辈。
特别在公元89年以后,因外戚上升到执掌大权而出现的政治生活的变化,使得保护关系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外戚大将军掌握的权力主要在于他们能够操纵对于数百名官员的任命。即使外戚的某些大将军也真心诚意试图招募一些受尊敬的人物,但是,人们仍有理由怀疑他们任命的人物,所以,一旦他们的外戚保护人垮台,他们通常被赶出官府。随着2世纪40年代梁家权力的巩固,许多官员和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开始相信政治上的决定不会对他们有利。由于试图找到种种办法来更使人们觉得他们拥有势力,他们开始强化他们自己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这最初表现在太学中,太学的门生在少数活跃的宗师的领导下,开始对官员的虐待提出抗议。
随着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结果出现为了获得渴望成为被保护人的人们的竞争。据徐榦(171—218年)记载,大臣、太傅、刺史和各郡太守不注意朝廷事务,而专心致志于他们的‘宾客’。[38] 足以在《后汉书》立传的重要人物在其经历中几乎都曾谢绝本地郡的职位或京城高级官员的举荐。这不是说获得这样的职位是不光彩的事情;倒不如说,人们希望担任和选择愿意接受的职务,并且在自愿的基础上和自己的上级保持关系。
任何被保护人所承担的一个义务就是在保护人去世时必须去吊孝,并且尽可能参加葬礼。被保护人后来还常常捐款立石碑。为公元161年去世的蓟州刺史立的石碑列举了193位“门生”,他们都来自他的管辖区域。泰山都尉孔宙(公元104—164年)的石碑是10个不同郡的43位门生——被保护人立的;4位部属来自他以前任职的地区;4位部属来自他的泰山衙门;10位门生来自八个郡,也许他们是真正的门生;一人是“以前的平民”。资深政治家刘宽(公元120—185年)的石碑列举了遍布华北华中各地的300多位门生——被保护人的名字,其中96位是当时在职官员,包括35位县令和11位太守。另一块单独的石碑列举了他“以前部属”的名单;这块石碑刻着从高官以下的50余人的名字。[39]
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单上看出关系网形成的途径。绅士们可以自行依附于他们本地或邻近地区的任何地方官吏,而成为他们的门生——被保护人或成为他们的下级官吏。这些地方官吏依次不仅同他们的上司具有公务的和私人的关系,而且也同其他正式官员、特别同他们以前的上司或保护人保持私人关系,而其中的某些上司或保护人依次又可能同朝廷里的重要人物有联系。在为高级官员或著名宗师送葬时,可能有数千名被保护人聚集在一起,以增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狂热关系达到极点时,人们甚至可能为只担任过他们几天太守的某人的母亲披麻戴孝。[40]
上层阶级增强的凝聚力和自觉性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自认为绅士(士)的人群扩大了。地方精英分子开始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士,即使学识平庸之辈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在地理上彼此分隔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集中于本地,他们仍然不仅从共同集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且也认为自己是全国的文化、学术和政治事务的参加者,即使是非常间接的参加者。[41] 在随后诸世纪中,“士”的上层阶级的力量和凝聚力被证明比起作为中国文明一体化基础的政治或经济的中央集权更为持久。
为了对地方精英分子表示尊敬而立的石刻碑文证明,绅士的理想扩大了。这时碑文表明地方精英分子共同具有表现在“笃行传”中的价值观——孝顺、敬服和淡于名利。当然,碑文并不表明人们实践了有教养绅士的所有这些美德,但是碑文确实表明人们共同具有一个绅士应该如何立言行事的自觉性。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82年的一块殡葬石刻,这件石刻看来是一个主要部属亲自撰写的。50000439_0687_1[42]
〔孔君〕年轻时学习过《礼经》。他遭逢人相食的普遍苦难时期,他构筑一小茅屋,因采集野菜赡养双亲而消瘦。他厚道、仁慈、直爽、朴素和忠诚,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他的一种天性,没有一件是他后天学到的。〔后来〕他境况稍佳,他想起他的祖母……他为祖母重作棺材,建一庙宇,在庙旁种植扁柏……他的幼弟品德善良,但不谙世务。〔孔君〕把幼弟请来和他住在一起四十余年。甚至自己借钱用时,他对弟弟却慷慨大方……他的美名四扬,县里请他当主簿,后又到功曹任职……[43]
可见,历代祖先无人作官、自己只当过下级县吏的人有权要求获得荣誉,因为他屡次尽孝道和为人慷慨大方。
地方精英往往以他们中间有一位具有这些特质的人物而公然自豪。南阳有58人全都是以前的下级官吏或赋闲绅士,他们捐资为当地一位学者或教师娄寿(公元97—174年)立碑。娄寿的祖父是正式官吏,但他的父亲却过着“安于贫困”的生活。娄寿本人被描述为好学,是一位善于与人相处而始终受人尊敬的热心人。他欣赏隐士生活和山间的雾霭,不巴结权势人物。他拒绝了郡县的所有邀请,不为高官厚禄的念头所动心。[44]
教育无疑是扩大有教养绅士理想的重要方法。一些正直的官员常常被描写为鼓励地方人民养成高尚的行为和学识的人。例如,何敞在任太守时,试图使该地的下级官员变成绅士。他不囿于严密的法律观点,而是按照《春秋》的原则判决诉讼案件。在他的影响下,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都回家去侍奉双亲,或者了却丧葬事宜。两百余人散发部分家财。有趣的是,何敞不是把文化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而是带到中原的一个贫瘠之地,即汝南。
其他官员非常强调熟读经书。将近汉末之际,当令孤邵任弘农太守时,该地没有一人熟悉经书(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宣扬例如公元175年的熹平石经)。因此,他征求一位下级官员到临近郡的一位老师那里去学习,当他获得基本知识以后,便要他当老师。另一些太守把有出息的人送到京城求学。例如,当杨终(死于公元100年)13岁是四川某郡一位低级职员时,太守赏识他的才华,把他送到京城。[45]
尽管荣誉应归于热心的县令和太守,但是好学之风似乎在整个后汉时期持久不衰。奖赏是丰厚的。在社会上,正式就学于某位宗师,此人便成为有教养的绅士;在政治上,这开辟了为官的门道。全国各地有专职学者和官员从事教学。《后汉书》几十处提到一些宗师拥有1000余名门生,还有更多的地方提到一些宗师拥有数百名门生。正史数次出现有天分孤儿的故事,他们虽然无力偿付学费,但却能遇到老师。这些故事被记载下来,以资鼓励人们,但它们也说明学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6]
上层阶级的自觉性由于文学著作而进一步加强,文学著作对于绅士中的个别人物或团体进行非难和评价。这些著作模仿在整个后汉时期流行的“笃行传”的某些惯例,而且它们表示了比较自觉和比较成熟的阶段。一个早期例子是孔融(死于公元208年)的短论,他的短论把颍川和汝南绅士的优劣作了比较,这两个地区在朋党运动中产生了许多领袖人物。孔融短论中保留下来的记载有如下述:[47]
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古代〕离娄并照者也。
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人们不仅对当时或本地的绅士进行评论,而且还撰写他们的传记。最初编辑这些传记的是赵岐,他在党锢期间被放逐。[48] 当由于叛乱而撤消他的放逐时,他担任军事指挥官,公元201年逝世时90余岁。他的著作《三辅决录》包括后汉期间他的家乡地区,即长安周围三个郡的人物传记。他对他家乡地区的绅士用这样的言论作了总结:“其为士好高尚义,贵于名行。其俗失则趣势进权,唯利是视。”④
当时一位年轻人王粲(公元177—217年)写了一本受欢迎的著作《汉末英雄记》。在随后一个世纪中人们继续大量写作这样的传记集。[49]
上层阶级演变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公元2世纪50至70年代的朋党运动。出身极为不同的人们响应朋党领袖的号召,因为他们已经自觉地成为绅士,因而对于国家的道德引导负有责任。这种政治议论的结局,即166至184年对于党人的迫害,又毫无疑问地增进了这些人的自觉性。尤其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大批善于辞令、精力旺盛、对政治感兴趣而又不能担任官职的人们。再也不能从人们的特性和相应的政治活动的标准来确定有教养绅士(士)的社会地位。许多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包括反抗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担任官职,不能把自己看成是政府机构的成员。作为他们社团的领袖和他们培育的价值观的支持者,他们唯一残存的作用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
按理来说,一旦被免职,鼓动者便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中央政府的心目中已经失宠,他们影响的范围将明显地收缩到他们家乡的城镇。但是,没有发生这种情形。党人在没有职务关系作为中介的情况下,保持他们在全国的联系。即使“有教养绅士”以前不完全了解他们自己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这一点现在已经是人人都清楚了。
汉亡于公元220年,这个年代不标志社会和经济趋势方面的任何变化。但是这个年代有助于观察过去两百年间发生的变化,因为北中国的两个新统治者曹操(公元155—220年)和曹丕(公元186—226年)采取了正式承认社会结构中的变化的政策。这一章指出两个主要变化:第一,地方社会的改组和农业生产的调整;第二,上层阶级这一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不依赖官府——它的成员可以去任职——的社会集团扩大和加强了。
曹操采用建立大规模农业戍屯军(屯田)的办法来对待已经变化的农业的社会基础。这种制度承认两种发展。第一种发展是贫苦农民不愿意或不能回到荒废的田地上去自己谋生。因为必需求助于掌握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人们的保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若干利益和放弃自己的许多自由,以换取自己的安全或幻想的安全。为了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曹操或者鼓励地主把他们的依附者安置在荒废的土地上,或者利用政府的力量把无地农民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聚落,把他们作为国家依附农民安置下来。这两种方针他兼而用之。李典(盛年期190—210年)拥有3000余名依附亲属和追随者,他被鼓励把他们安置在河北南部遗弃的土地上。[50] 在其他地区,移居者是由政府分配到那里的半复员的士兵。
导致这种安置政策的第二种发展是政府需要增加除人头税之外的岁入。忽视大庄园主的经济和社会实力(他们能够全面抗税,同时把大部分税收转嫁到个体农民身上),简直等于减少收入。曹操却另有办法,他模仿庄园主,像他们那样雇用佃户和依附者来获得收入。因此,即使不能完全控制豪右,税吏对他们的财产和田产又无能为力,政府仍然能够从“官田”上获得固定收入。[51]
曹操和曹丕鉴于上层阶级结构的变化,改革了官员招收制度。这种新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后来因它使得名门豪族出身的人们享有莫大优惠的贵族偏向而闻名。但是,起初它对于上层阶级的自治似乎是一种让步。地方舆论关于个别人的一致意见被认为是挑选公职人员的适当的根据。[52] 在每个郡县,地方上一位声望很高的人物负责对当地绅士按照其才干和正直的名气进行评价。政府就按照这些评价来任命公职人员,因而默认上层阶级自行吸收成员和自行证明合格。在以前的半个多世纪期间,各级官员由于害怕主要文人学士和有教养绅士的嘲笑,他们的行为还有某种范围的克制。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他们评价的合法性得到承认,但是他们一旦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同时被授予选拔不受评论的候选人的责任。
[1] 从村社的角度或者从村社关系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日本学者几乎都认为这些变化是当然的。简短的英文讨论见平中苓次:《田租》,第67—69页。也见以上第10章。广泛的分析见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东京,1978),第33—36、123—158页。也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东京,1960);川胜义雄:《汉末的抵抗运动》,《东洋史研究》, 25∶4 (1967),第386—413页;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第403—444页。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的中国学者常常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论述。见贺昌群:《汉唐土地所有制》,第131—211页。
[2] 《后汉书》卷七七,第2489页。关于蛮横的地方血缘集团更多的例子,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敦,1972),第455—459页。
[3] 《隶释》卷三,第4—9页。
[4] 见以上第5章《叛乱与战争》;第16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5] 霍华德·利维:《黄巾教和汉末的叛乱》,《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6∶4(1956),第214—227页;石泰安:《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页;关于这些运动中宗教和思想的含意,见以下第16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6] 《三国志·魏书八》,第263页以下。也见上文第5章《曹操的晚年》。
[7] 关于这个问题,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1955),第3—29页;见贺昌群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关于宗族宗部的商榷》,载《历史研究》,1956.11,第89—100页。
[8] 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第443—450页。
[9] 《三国志·蜀书一》卷三一,第866页;《三国志·蜀书十一》卷四一,第1007页;《三国志·魏书十一》卷五六,第1309页。
[10] 例如,见《三国志·魏书十一》卷十一,第340—341页,关于田畴(公元169—214年)的功绩:他把五千余户避难家庭组织起来,赢得它们的父老赞成二十余条法律。
[11] 关于公元220年以前制止刘节专横行为的企图,见《三国志·魏书十二》卷十二,第386—387页。
[12] 关于这种区别,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5—472页;贺昌群:《汉唐土地所有制》,第166—211页;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63—249页。
[13] 《全后汉文》卷十三,第5页。桓谭著作残篇译文载蒂莫特斯·波科拉:《〈新论〉及桓谭其他作品》(安阿伯,1975)。关于引证的这节文字,见第15—16页。
[14] 见《风俗通义》卷三至五。关于《后汉书》中复述轶事的传记的例子,也可在《风俗通义》中找到,见《后汉书》卷五三,第1746—1750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294—1295页;《风俗通义》卷三,第8页;卷五,第10、11页;卷四,第11页。
[15] 《后汉书》卷二七,第930—931页。
[16] 《后汉书》卷四一,第1477页。
[17] 《论衡》三十(《自纪篇》),第1196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80页)。
[18] 《后汉书》卷四九,第1629页。
[19] 《论衡》十二(《程材篇》、《量知篇》和《谢短篇》),第535—577页(福克:《论衡》第2卷,第56—85页)。
[20] 《论衡》十二(《程材篇》),第547页(福克:《论衡》第2卷,第65卷)。
[21] 《潜夫论》八(《交际篇》),第335、337页以下。
[22] 《潜夫论》一(《论荣篇》),第34—35页。关于丹,见高本汉:《书经》,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22(1950),第11页。
[23] 原书缺注。——译者
[24] 《后汉书》卷十八,第675页以下;《后汉书》卷四一,第1395—1403页。
[25] 《后汉书》卷五八,第1865页。于定国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后汉书》卷七一,第3041页以下。
[26] 《后汉书》卷四八,第1614页;《后汉书》卷三一,第1109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23页。
[27] 《后汉书》卷四六,第1543—1546页。
[28] 埃伯里:《后汉石刻碑文》。
[29] 《隶释》卷五,第15—23页。
[30] 《后汉书》卷二四,第838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5—1527页。
[31] 《隶释》卷十二,第7—8页。
[32] 《后汉书》卷三五,第1207页。
[33] 《隶释》卷一,第1—4、8—13页。
[34] 《两汉金石记》卷十二,第1—7页。
[35] 《两汉金石记》卷十一,第11—17页。
[36] 三份发起人名单中(每一份包括100多个姓名),只列举姓苏、姓尹、姓沈和姓田的人物。由于这些姓名不如在这里没有列举的李、杨、王、张那样普遍,他们可能是真正的亲戚。
[37] 关于详细情形,见埃伯里:《后汉时期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3∶3(1983),第533—542页。
[38] 《中论》B,第23页。
[39] 《隶释》卷七,第1—2、4—7页;《隶释》卷十一,第1—6页;《隶续》卷十二,第5—8、18—21页。
[40] 《风俗通义》卷三,第2页。
[41]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从思想史的观点讨论了这个问题,《新亚学报》,4∶1(1959),第25—144页。
[42] 《隶释》卷五,第5—7页。
[43] 引文系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44] 《隶释》卷九,第9—12页。
[45]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7页;《后汉书》卷四八,第1597页;《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第54页(见裴松之的注释)。
[46] 关于学习制度的确立,见以下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47] 《全后汉文》卷八三,第10—11页。
[48] 见以上第5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49] 关于王粲,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卷二一),第597页以下。这些后汉著作没有一部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其中的片断被大量地引证于其他史书,特别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峻的《世说新语》注;关于《英雄记》的引文,见《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3页,注1;第2374页,注2;第2375页,注3;关于《汉末名士录》的引文,见《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6页,注2。关于《三国志》,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关于《世说新语》,见理查德·马瑟:《世说新语》(明尼阿波利斯,1976)。
[50]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十八),第533—534页。
[51] 关于这种政策,见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模式》(伦敦,1973),第35—41页。
[52] 关于这种制度,见唐纳德·霍尔兹曼:《中世纪中心制度的起源》,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Ⅰ(巴黎,1957),第387—414页。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